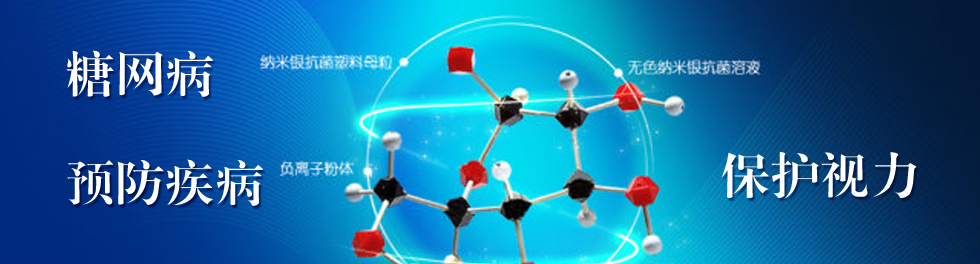一分半
那个红灯有一分半的时长。还好。
张之初是硬数出来的,无聊。他像木板被钉在路口,微张的嘴宛如青杏。相貌平平,身材不够出挑。像流水线上的产品,千篇一律的式样。没有出处没有标识,但好在是清醒的。
太阳很毒,光线是不要钱的,无情又阔绰地当头照射,蔓延到地面。张之初觉得那是滚烫的辣椒油,一束一束地,灌溉着芸芸众生。他觉得自己站在这里很愚蠢,等着两个四个轮子的机械吐着气地挪过去。他又觉得自己没必要这么急,又不能催着一分半快点流淌,像妓女一样。
他手里拎着刚买的鲫鱼,要回去炖汤的。他晃了晃袋子,没死;一条鱼躺在另一条鱼上,亮晶晶的鳞片凹凸不平,他觉得是很恶心的画面。
九岁时张之初还不知道性是什么,要是不小心牵到同班女生的手,他会担心她是不是会怀孕,才会悄悄告诉她“你手刚碰到了脏东西哦,快去洗手”。他现在想起来,心里的笑像开水不小心沸腾地蒸散开来,直到李治经把他拦腰截断。李治经第一次压在他身上的时候,他觉得是痛的、滋润的,只是没有多大意思。他努力地说“舅舅,我不会。”李治经还是塞了进来。他慢慢可以说话之后,他说“对不起”。李治经像数学老师在他考差后说的一样“没关系,你还有很多进步空间”。
张之初轻轻揭开包裹两条鲫鱼的塑料口袋,那个红灯连成一条虚线,串联起和李治经存在的所有时间和空间。好多碎片像空气一样,以背对的姿态翻滚成一张张皱巴巴的床单。他仿佛听见自己的心在枕头里尖叫,棉絮泄露出饱满的分贝。他分不清是李治经冲撞了他的躯壳还是他舔舐了李治经的伤口,他分不清李治经每一次挤出来的是汗水还是什么黏糊糊的液体。他不懂那是什么,他还没有学过生物。
张之初唯一记得的是,在任何时间和地点,李治经都是压在他身上。李治经仿佛驱车在他身上行驶,他听见发动机噗噗作响,车门砰地一声夹起,他总有一种被甩巴掌的感觉。他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,只知道一定是人生最终极的恶俗的真谛。
十一岁时张之初想起来了,百科全书里说过水蛭。李治经就像光盈盈的,水里钻出来的水蛭,抽长了,又缩短了;抽长了,又缩短了,一寸一寸地在他身上移,吸附着吮蚀着他,直到最后一刻钻进他的心,泄力,然后倒下了。他想,“这是舅舅爱你的方式”。
十四岁之前很久张之初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。他想了个法子,他在网路上找到了有病的人,说“你给我一次,我的病就好了”。上场前他慌了,他洗了个热水澡,把积郁都冲掉了,一上去就好了。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。张之初不再是那个赝品了,他向李治经卖弄着战利品——他的身体,像挤牙膏一样干瘪的身体,但他还是觉得裂痕阴凉地从足底爬到了大脑。
张之初想他最后还是胜利的,他坚持到了最后。李治经不会找他了,李治经才是那个脆弱的可怜的人,李治经需要他,李治经需要钉着他,简直需要时时刻刻坦着阴茎在他跟前晃。发育的少年可以轻而易举令男人疯到天亮,李治经失去了这个美不胜收的凭借。
难道还要同情这个男人吗?“反正就是我什么都不懂。”他对自己说。又无端地质问着“一分半这么长吗?”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像狩猎时被射中的飞鸟被日光缠绕着坠落下来,却找不到猎人是谁。
鲫鱼在挣扎着呼吸,那个红灯拉长到永恒的这一瞬间,映衬着一片白色的炽热的天光。张之初的侧影歇落在口渴的喘着气的柏油路面上,他的睫毛像米色的蛾翅。旁边谁的手机响了,铃声在半空中承载着一辈子的沉浮,听上去竟有种缥缈。
等待过街的人越积越多。十五岁的张之初彻底明白了性侵这个词,原来不是一种畸形的寄生关系。但他觉得李治经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,驾驭他。他恨他,到底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,只是有感情。他们才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,虎与伥的关系,是恶俗的占有。他这才生是他的人,死是他的鬼。
一分半过去了。马路上的人开始奔跑一样地行走,在街这头的人们穿过去,在那头的人们穿过来,像夸父逐日,像天空中熙熙攘攘的麻雀。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好人比真人多,坏人最少。他永远是坚强的,聪明的,胜利的。
但他一走神,李治经的影子虚化成有尾巴的黑猫,徐徐波动着。它出现在拥挤的人群缝隙,沿着斑马线慢慢走,不朝左看,也不朝右看,它自顾自地走过去了。
十八岁的张之初风华正茂,被关在世界外面一分半,不朝左看,也不朝右看。
生命自顾自地走过去了。
请
文字:鱼香肉丝
图文排版:caroo
图片:堆糖网
赞赏
人赞赏